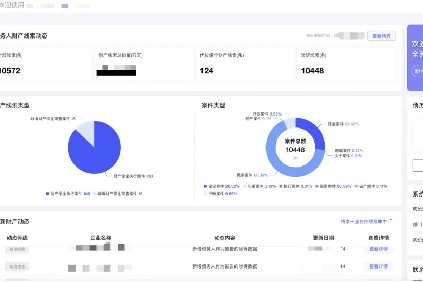作者:為睿房地產金融部
來源:為睿資產(ID:VeryAsset)
2013年以來,“互聯網+”和不良資產是資本市場上持續度最久、關注度最高的題材,但是兩大題材卻呈現出了截然不同的市場景象。
2013年被譽為“互聯網金融元年”,2014年開啟互聯網創投熱潮,2015年則被譽為“互聯網行業并購年”,2016年創投回暖仍然看好互聯網題材,2017年互聯網投資在新常態下轉向“新技術、新布局”,2018年互聯網金融亂象導致金融科技的崛起或回歸,但金融科技未來何去何從,當下卻似乎并無定論。
同期,不良資產也是各路資本高度關注的“逆周期”投資熱點。從2014年開始的地方AMC批籌設立,政策引導和市場共識都認為不良資產是無可爭議的投資熱點,但是“年年歲歲談進展,歲歲年年無突破“。
相較于其他金融領域,不良資產處置略顯無聊,既沒有鬧出吸引眼球的大新聞,也沒有頻頻被監管層直接點名,在科技浪潮中更無炫技。市場上以AMC為代表的持牌機構玩家在處置端普遍缺乏活躍度,而更熱衷兩頭在外的通道業務,這種違背AMC設立初衷的業務已被監管部門三令五申的叫停;政府推崇的債轉股項目和紓困基金也在幾個試點項目之后顯得“雷聲大,雨點小”;傳統大資金玩家包括外資玩家更偏愛大宗交易這類“有熱度,沒廣度”的明星項目。而市場上大量存在的批量或零售不良資產都最終面臨著處置死結,不良資產的出清通路被堵住,導致市場長期處于“淤積”狀態。同時,泛金融領域的不斷爆雷和“二次不良”項目的不斷涌現加劇了這種狀態,項目方和資金方之間既想“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卻又被現實無情摧殘得“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
一、孤立無援的項目方
市場普遍認為,本輪不良資產周期開啟以來,至今尚未達到拐點,未來兩三年不良資產供給仍難以出現下降,不良資產總量會在合理區間繼續有所增加。
不良資產的初始供給側主要包括銀行、信托、金融租賃等金融機構,其次是互聯網借貸平臺,還包括廣義的影子銀行機構等,基于資產質量、撥備計提和利損考核等壓力,機構往往對不良資產的轉讓售賣定價過高,與市場定價相去甚遠,加上不良資產投資的天然劣質性和復雜性,導致機構組織的各類不良資產推介會有價無市。
近年來,監管對不良資產行業的要求越來越高,從主體資質、操作流程、合規要求、從業資格等方面都作出了較為明確的規范。從2018年2月28日,中國銀監會下發《關于調整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監管要求的通知》(銀監發【2018】7號),明確單家銀行逾期90天以上貸款納入不良貸款的比例,到要求屬于銀保監會直管的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要求在2018年6月30日之前,“一刀切”將全部逾期90天以上的貸款計入不良,反映了監管管層對不良貸款監管口徑的進一步收緊,也將進一步促使存量信貸資產質量分化,加速不良資產的涌現。最新的《關于加強地方資產管理公司監督管理工作的通知》(銀保監發【2019】153號)再次明確要求各AMC回歸本源,專注主業,同時要求各AMC不能簡單脫離不良從事債權業務,變相從事項目融資,不能通過私募債等向公眾融資擴大杠桿,以及未來AMC面臨的更嚴格監管處罰,使得原本寄望“以時間換空間”的通道業務空間越來越小和其他騰挪隱藏不良資產的手段越來越少,這將進一步加大不良資產市場的供給。
不良資產市場的天量存量和可預計的持續增量,事實性地造成了不良資產市場供給側的堆積,而去化側并未隨市場需求得到根本性改變,不良資產形成了大面積的價值洼地,價值發現成為共識。于是,“錢在哪兒?”成為了資產方或者項目方最為關注、也最為頭疼的問題,這時,傳統抱殘守缺、缺乏專業支撐的項目方在虎視眈眈的資金方中顯得特別孤立無援。
二、愛莫能助的資金方
傳統的“三打”思維與“悶聲發大財”的心態折現了資金方對不良資產領域的不熟悉和不專業。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不良資產投資只需要簡單打折批量地收購,再進行拆包零售,躺著賺差價就可以了。的確,不良資產的轉讓處置一直是AMC重要的傳統處置方式和手段,但日趨激烈的競爭環境已將AMC的角色推得更遠,也對社會各類資金參與方的要求提得更高。面對近貳萬億級的不良資產大蛋糕,無論是在債權層面還是物權層面,諸多資金躍躍欲試,垂涎不良資產處置背后蘊藏的豐厚利潤。
但是,市面上大量的資金方,尤其是想通過不良資產處置“撿便宜”的物權類資金方對不良債權本身的不確定性難以接受,這些不確定性主要體現在:
1.債權轉讓方無披露債權瑕疵的義務。不良債權普遍存在債權效力有爭議、實現債權有障礙等瑕疵。債權隱含的瑕疵基本由買家自行盡職調查,賣方只需對債權的客觀狀態進行描述,提供能夠證明債權存在的材料而沒有義務披露債權的瑕疵;
2.債權能否實現的風險由買家承擔。在通常的債權轉讓關系中,轉讓人不保證債權的有效性、完整性,不保證受讓人可以實現債權,不保證實現債權的時間和程度;債權不能實現的風險由受讓人承擔,不得向轉讓人追索;
3.債務人往往對抗性較強。不良債權的債務人通常有一套應對債權人追收的辦法,除日常的轉移財產、逃避債務外,債務人在案件訴訟和執行中無論程序或實體上均設置種種障礙,對抗之強非一般訴訟、執行案件可比;
4.債權價值實現程度的差異性較大。由于應對債務人對抗的能力不同,同一筆債權能否實現,由不同專業技能的人員追收的效果有可能千差萬別,實現的價值差異程度很大;
5.不能完全實現債權幾乎是普遍現象。債權能否實現,受債權存在效力瑕疵、時效瑕疵,或債務人喪失償還能力,抵押物存在瑕疵,第三方干預等諸多因素的影響。通常,損失類的債權包中,絕大部分債權均無可能追收,資產包的價值主要靠包中一二個“重點項目”的回收。
對不良債權不確定性的排斥心態和對不良債權對應抵押物上各種復雜的司法、行政,甚至是人際關系的無能為力,加上不良資產本身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和門檻過高的處置難度,物權類資金方對化解金融風險、消減不良存量顯得愛莫能助。
三、不良資產處置服務商的演進
不良資產的處置變現,是整個價值鏈最值得琢磨的環節,也是最值得付出的環節,因為是行業的最終出口,資產處置消化能力將成為從業機構的必備生存技能。這其中,不良資產投資者對價值鏈條上處置服務商的需求就必不可少,主要的處置服務商包括催收機構、拍賣機構、司法體系、會審機構、稅務機構等。
不良資產處置是指通過綜合運用法律允許范圍內的一切手段和方法,對資產進行的價值變現和價值提升的活動。無論是不良資產的階段性處置還是終極處置,對“一切手段和方法”的需求,都推動了處置服務商的演進。
1.處置服務商的專業賦能
不良資產處置的市場準入及專業要求較高,“投行化思維、基金化運作、產業化退出”的理念得到了行業認同,這對投資者對處置服務商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在階段性處置中涉及到的評估盡調、債轉股、債務重組、訴訟保全、以資抵債、資產置換、企業重組、實物資產再投資完善、實物資產出租、實物資產投資等方式方案的設計,在終極處置涉及到的破產清算、拍賣、招標、協議轉讓、折扣變現等方式方案的把控,都需要處置服務商的專業賦能。
2.處置服務商的科技賦能盡管互聯網+不良資產的模式還未走通,但處置服務商對處置鏈條中的諸多環節已經進行了深度科技滲透,這在智能客服、陽光催收、網絡拍賣、協作平臺及數據修復及存證等領域都得到了充分體現。諸多科技手段的應用,對提升行業規范水平、防止暴力催收、提高信息透明度、去屬地化等方面起到積極的作用。
3.處置服務商的信息賦能
為不良資產處置提供信息是處置服務商存在的基本價值。處置服務商在資產購買前的盡調、定價,購買后的處置、外聘其他服務機構,潛在投資者找尋和資產的推介,資產處置難度及進度的反向評估,前手交易價格的查詢及稅務籌劃,司法資源的協同等,都是處置服務商的信息賦能。
4.處置服務商的金融賦能
傳統不良資產處置的服務商,并不直接參與處置中的資金活動,但這種以費用性第三方的出現的形式,很難使服務商做到投前盡調分析和投后運營管理的最大化努力,也難以更好的為資金資產方提供最優服務。服務商的金融賦能,要求其在解決不良資產處置過程中的優先級資金匹配,或劣后級資金發掘,并利用專業處置能力,促進二者在同一個項目上達成共識。
結 語
以不良資產投資為典型代表的特殊機會資產投資本質上是一種非標另類投資,投資就要解決的兩大問題: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問題,投資者往往寄望發掘不良資產的特殊價值進而實現超高收益來進行覆蓋,而特殊價值實現,必須建立在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基礎上。
解決不良資產處置中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一要解決投前存在的逆向選擇問題;二要解決投后可能產生的道德風險問題;三要解決可能產生的委托代理過程中的代理人問題,尤其是司法委托代理關系。不良資產投資與處置行業作為一個法律與金融知識與技能高度融合的行業,亦要求行業處置服務商不斷演進,既要扮演好傳統服務商的角色,還要深度參與不良資產處置的投后管理,通過后端收益分配獲取更高的報酬,以便讓專業處置服務商的價值得到最大限度的體現,在不良資產藍海中更好地拉近項目方和資金方的合作。也許,不良資產項目與資金之間真的只差一個專業服務商的距離。
注: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資產界立場。
題圖來自 Pexels,基于 CC0 協議
本文由“為睿資產”投稿資產界,并經資產界編輯發布。版權歸原作者所有,未經授權,請勿轉載,謝謝!




 為睿資產
為睿資產